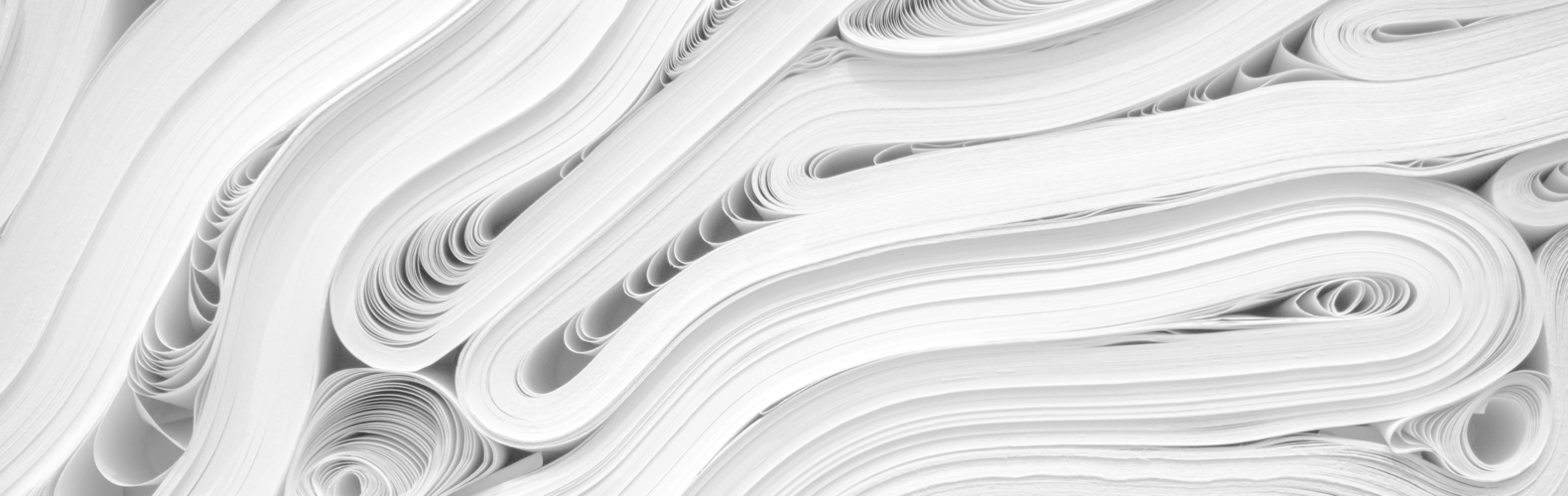随着数据、算法、算力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围绕人工智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创作表现,以及人与人工智能交互等话题的探讨日益热烈。技术迭代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已不再停留于理论设想,而是真切融入现实生活,成为一种全新的内容创作、呈现与交互模式。
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创作,已然跨越科学领域,浸染文化领域,继而在法律领域带来挑战。机器创作过程中“输入—学习—输出”三个阶段,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著作权景象,这是一种与传统有别的“或然世界”或者说“后人类境况”。其间所引发的著作权问题,可以概括为“机器读者”“机器作者”以及“机器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无论是“输入”阶段的数据挖掘,还是“学习”阶段的算法创作,以至“输出”阶段的作品生成及其权利归属,诸多问题不仅与已有法律秩序形成冲突,甚至会颠覆我们业已形成的法律认知。[1]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著作权保护这一关键话题,我将从以下几个要点展开深入研讨。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该规定表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满足以下四个要件:(1)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2)具有独创性;(3)能以一定形式表现;(4)属于智力成果。
部分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既然与人类智能创作物具有外在的不可区分性以及内容上的相似性,作品的独创性不仅需要考虑自然人创作的过程,而且需要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最终结果是否属于思想的表达,能够反映一定的思想、情感,表达一定的信息。故其应当获得与人类智能创作物平等的机会,即认可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认为,“算法创作的作品是机器作者(智能机器的开发者或操作者)与人类作者合作创作的作品,是智能版权时代合作作品的特殊类型。创作者身份不应是作品受保护的构成条件。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与人类创作作品,在思想表现形式即作品外观方面难以区分,它们只要满足独创性要求,即可能具备可版权性。”[1]
部分观点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须为人类的创作成果,从立法目的来看,只有人才能理解著作权法并受到激励,因此,只有人的创作成果才能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否认AIGC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学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或对象应当是人类或者说自然人从事智力劳动的产物,而不能是借助于人工智能完成的。
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认为,“ChatGPT生成的内容仍然是直接应用某种算法和规则的结果。只是它更多地应用了概率论,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训练,以巨大的计算量计算词与词之间搭配分布的概率,并对用户输入文字进行合理延续。这仍然与人类的创作存在本质的区别。”[2]
个人认为,AIGC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首先,AIGC符合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的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客体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著作权法》中作品的独创性要件、《专利法》中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三性”要件。从理论上说,只要AIGC满足了相应的知识产权客体的条件,就没有理由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其次,AIGC是人类智力活动和智力劳动的产物,与自然人从事创造性行为所得的结果存在实质性相同。AIGC固然是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的,但其与自然人从事创作和发明创造所形成的作品或发明创造在外观和内容上并没有实质性差异。
(二)如果AIGC属于作品,应如何认定其著作权归属
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中,主体资格的取得大抵有两种情形:一是通过智力创作的事实行为而成为主体的自然人作者,二是基于法律规定的主观拟制而视为主体的法人作者。人工智能基于深度学习而生成具有作品外观的思想表达,这种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自我输出成果的过程,似为某种意义上的创作,但在著作权法框架里无法成就其主体资格。在民事主体理论中,“自然人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资格,而“拟制人格”是法律对自然人的集合体即法人所拟制的主体资格。
在我国,围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问题,学者们综合多维度视角展开深入探究。从“算法创作”中意志体现的剖析,到“机器作品”生成机理的钻研,再到实质性贡献原则的衡量以及利益平衡理论的运用,基于这些不同层面的考量,法学家们提出了诸多独到且差异化的见解。
观点一:“作品——著作权说”,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为具有独创性且有人格要素的作品。在人机合成创作的情况下,“机器作者”与人类作者都对作品作出实质性贡献,其著作权归属可参照法人作品规定或创作者约定处理。[3]
观点二:“投资——邻接权说”,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源于投资人的“非创作性”投入,投资人的利益理应成为重点保护对象。从广义上来说,邻接权的客体涵盖了那些具备思想表达,但又未达到作品标准的内容。因此,依据 “额头出汗原则”,法律应当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同时,还需体现出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产物在法律保护方面的差异,即要将智能设计者的权利与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区分开来。而智能生成内容所享有的权利,其实就是旨在保护投资人利益的邻接权。[4]
观点三:“孳息——所有权说”,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属于物的范畴,无法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适格主体。其产生的内容从性质而言,呈现出一种“物生物”的关系。与之相对,传统著作权法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则是“人生物”的模式。从民法学角度解释,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可被视作“知识财产孳息”,即机器创作物是独立于人工智能而产生的知识财产孳息。至于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问题,可认定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使用者或者所有者为著作权人。[5]
针对以上三个观点,吴汉东教授更倾向于:“作品——著作权说”,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建构“作者—著作权人”的二元权利主体结构,对创作主体资格与权利主体资格实行界分,即作者未必是第一著作权人。鼓励作品创作与传播的立法宗旨,不会因为创作者是人类还是机器而有所改变,但基于著作权法激励功能而产生创作动因,能够践行立法宗旨的权利人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
AIGC 版权归属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答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如果AI生成的内容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则可能归属于人类创作者;另一方面,如果AI生成的内容仅是基于已有数据的机械处理,则可能不享有著作权保护。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法律的完善,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更明确的解决。[6]
(三)案例分享:江苏首例、全国第二例AIGC著作权侵权案[7]
近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江苏首例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构成(美术)作品的判决,判决认为,体现创作者智力劳动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具备独创性,应当依法保护。这一判决不仅是江苏省的首例,还是全国第二例确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具有著作权的案件。
基本案情:AIGC创作者林晨于2023年2月14日通过AI工具(Midjourney软件)创作了作品《伴心》。该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爱心”元素与情人节的融合,林晨反复训练AI绘画工具,通过修改输入的提示词,并将AI生成的半成品提取出来用PS软件手动“加工”,最终完成了作品。作品中,红色水滴与水面上的倒影共同形成完整的爱心,寓意爱因陪伴而完整。
2023年11月,林晨发现杭州某技术公司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次发布爱心气球模组安装视频及图片,其中图片内容与《伴心》内容相比,除了图片长宽比、气球表面文字、倒影对应的东方明珠存在差异外,其余部分完全一致。同时,常熟某房地产公司在其一则微信推文上使用了该照片,并在其开发的商业区湖面内,建造了半个爱心气球的立体装置。
林晨在与对方沟通无果后,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杭州某公司和常熟某房地产公司停止侵权,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50 万元等。
图为原告林晨通过AI交互设计生成的图片作品《伴心》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晨对提示词的修改、通过图片处理软件对图片细节调整体现了其作为作者的独特选择与安排,以此生成的平面图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明确Midjourney软件用户协议约定使用软件服务生产图片作品的资产及其权利属于用户,两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该图片进行网络传播构成侵权。判决同时指出,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应限定于该图片,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仅以“爱心”为基础进行实体建造不属于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如此判决避免了著作权的过度保护与权利滥用。最终常熟法院判决:一、侵权方在其小某书账号连续三天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万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服判息诉,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针对该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孙平教授表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本质上是技术创新与法律规则碰撞的缩影。全球范围内,从学界到司法与执法部门,以往多持“全有或全无”的二元立场,但近年来随着生成式AI的普及,学界与实务界开始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光谱式”认定标准。常熟法院在本案中精准捕捉到这一转向,将法律评价聚焦于人类在“提示词设计—迭代调整—后期加工”全流程中的智力投入。
著作权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需与时俱进,契合技术发展的步伐。它有着特定的立法目的与精神内核,通过赋予作者专有权利和对这些权利提供法律保护,以此激励作者投身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以人为本” 这一理念贯穿于著作权法的始终,作品自诞生之初便与人类作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正如王迁教授指出的那样,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工智能变得如此强大,任何人基于其心智和情感创作的作品,都无法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相媲美,以至于这个世界不再需要人类进行创作,那么人类所做出的正确的选择,也不是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纳入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范围,而是承认著作权法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因为不必再通过著作权法鼓励任何人的创作。到了那一天,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为作品的讨论恐怕比今天更加没有意义了。
参考文献:
[1]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吴汉东,《中外法学编辑部》,2020年第3期
[2] 《再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王迁,《政法论坛》
[3]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熊琦,《知识产权》2017年第3期;《人工智能‘创作’的人格要素》,徐小奔,《求索》2019年第6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孙山,《知识产权》2018年第11期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理论证成与权利安排》,许明月、谭玲
[4] 《孳息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权利归属》,黄玉烨、司马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3-29页;《版权制度应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路径选择》,林秀芹、游凯杰,《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6期
[5] 《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作品版权认定分析报告》,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6] 《为漂泊的“AI心”找到司法归属》,中国法院网
[7]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著作权保护》,郭禾,冯晓青,张平,熊琦,张吉豫,人民法院出版社
[8]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版权产业发展的法律保障》,易继明
黄璐,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主要业务方向:民事纠纷、商事仲裁
联系电话:18352538784
电子邮箱:1056945020@qq.com